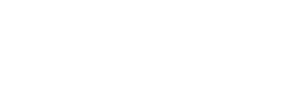[1]张鹏卜:《周至县名考义》,《中国地名》2018年第12期,第24-26页。
[1][清]知县杨仪重修《盩厔县志卷之一》,《中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9),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
周至县秦岭以北地区地形西南高东北低,东、中部平原与秦岭泾渭分明,西部平原与秦岭之间有个黄土台原的过渡地。盩厔山最初应指盩厔县西部的黄土台原地。盩厔县因盩厔山而得名,盩厔山之所以逐渐被人遗忘,正是由于称原坡为山的习惯只是本地所特有,随着与外界的交流扩大及移民等因素,称原坡为山的习惯在盩厔县等地方逐渐消失,人们也忘了盩厔山的源地了。
二、盩厔“二曲”源地考
盩厔县因盩厔山而得名,但“盩厔”一词的含义不明。到了唐代,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中以“二曲”解盩厔:“山曲曰盩,水曲曰厔。”[1]“二曲”说产生后,对宋、元、明、清的诸多古籍产生了重大影响,“二曲”说影响越来越大,以至于成为盩厔县的代称。
周至县发源于秦岭北麓的河流较多,曲折注入渭河,言周至县“水曲”倒也说的过去,可与那些处于群山环绕中的中国数百个县市而言,周至县绝大多数人口生活的北部平原地区,其北部并无山峦。如果说“山曲为盩”,周至县周围山的曲势在陕西省也进不了前30名,更不用说全国了。周至县位于渭河以南的关中平原,秦岭在正南方高耸挺拔,东西向一字排开,整体而言,并无曲势。“二曲”之说,其立足点为适宜人口较大规模聚集的城邑,必在周至县秦岭与关中平原的过渡地带。如果说周至县北部平原有曲折山势的局部地形,非周至县西南部的竹峪一带台原地区莫属。
竹峪镇南部为秦岭山区,北部是丘陵台塬,泥峪河、沙河、阳化河、干甘河、仰天河等河流从南向北流过。周至县东中部的秦岭与关中平原几乎没有过渡地带,秦岭自东至周至县西南部,竹峪原向关中平原突出,原内沟壑连绵,与黄土台原类似。因此,唐代李吉甫的盩厔“二曲”说,其源地应在周至县竹峪原一带,我们以此为视角观察竹峪原地周围一带的地形做出了上述的描述应该是能自圆其说的。
“二曲”说形成后,“二曲”说观测点发生了分化,在许多人的认识中,由竹峪台原一带转移到周至县东部终南一带,因为周至县东部发源秦岭注入渭河的河流更多,周至县东部河流纵横的地形更符合“水曲”的特点。由此,“二曲”说也演变为“重水轻山”,进而误以为“山曲”中的“山”为终南镇以南的秦岭山了。
[1][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1页。
三、“盩厔”词义考
盩厔“二曲”之说影响虽大,但并不是唯一的含义。《说文解字》中对盩的解释是:“盩,引击也。从㚔攴,见血也。”[1]“诸盩”是周人的先祖之一。《史记》载:“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索隐曰:《世本》云:‘太公组绀诸盩。’《三代世表》称叔类,凡四名。皇甫谧云‘公祖一名组绀诸盩,字叔类,号曰太公’也。”[2]诸盩是古公亶父的父亲,古公亶父生季历,季历生文王。
《周礼》载,“先代创业之主,唯周追王,夏殷以前,未有闻焉。显考以下谓之亲庙,亲庙月祭,属近礼崇。周武王时,诸盩为显考庙。周人以讳事神,固不以追王所不及而阙正庙之讳也。[3]“王立七庙,曰考庙、曰王考庙、曰皇考庙、曰显考庙、曰祖考庙,远庙为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迁,二祧以盛德不毁,迭迁之议其在四庙也。”[4]
诸盩是周武王的高祖父,是公叔祖类庙的讳称。建立沣京以前,周人的政治中心在漆水河流域。东进以前,周人在漆水河流域建有宗庙。建立沣京以后,在沣京新建宗庙,而漆水河流域的宗庙应还会保留。“王立七庙”制源自西周,始于文王或武王,也可能是古公亶父或季历,而将公叔祖类庙讳为诸盩。问题是,周武王去世以后,周武王会有自己的新庙,而其高祖父诸盩的庙就要迁移,这也是西周王朝建立后第一个要迁的庙,诸盩庙迁到沣京的远庙,还是漆水河流域的远庙,迁到旧政治中心的可能性自然就会更大些。
至此可以确定,先周、西周时期,诸盩是周武王高祖父庙的称呼,可以称为盩庙。“厔”在古籍中也作“庢”,是“室”的变体,周代室、庙、宫有互通现象。[5]所以盩室就是盩庙,极有可能为了突显盩室——周王先祖宗庙的神圣性,将“室”变为“庢”,后来又省减为“厔”,这应是盩厔二字的最初由来了。
1978年5月扶风县齐村出土的作于周厉王十二年的《㝬簋》上的金文,印证了古籍的记载。铭文中有这样的记载:“(肆)余以□土献民,爯盩先王宗室;□作□□宝簋,用康惠朕皇文列祖考。”
[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成都古籍书店1981年,第526页。
[2][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4页。
[3][北宋]王钦若:《册府元龟》,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979页。
[4]钟文烝:《春秋毂梁传补注》,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97页。
[5]王启敏:《周代宗庙礼制考》,《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50页。
铭文中的“盩先王宗室”即为“盩室”,即宗庙。诸盩庙是西周王朝第一个迁移的正庙,盩可能成为周王室远祖的代称,周厉王以“□土献民”的方式纪念远祖,而作此宝簋来纪念他的近祖“皇文列祖考”。也可能“盩先王宗室”与“皇文列祖考”的意思相同,均为周先王宗庙之意,周厉王以“□土献民”和作宝簋两件事来奉祀他的祖庙。总之,盩厔就是周先王宗庙之意。
四、“盩先王宗庙”与周至县
今天周至县竹峪一带在汉代以前有盩厔山,说明此地曾建“盩先王宗室”。此庙可能建立较早,与渭河以北的宗庙并存,也可能是犬戎等进攻西周,渭河以北的宗庙南迁等其他原因所致。至于盩庙的具体位置,有待发现。
盩庙建在周至县竹峪一带,是因为周至县在先周时期是周人的核心活动地域。周人始祖后稷在武功县的漆水河谷一带生息,城邑为周城。“《括地志》云:‘故周城一名美阳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北二十五里,即太王城也。’”周原位于漆水河的下游,距离渭河很近。漆渭之会正对周至县竹峪一带。史书记载周人后来北迁豳地。即便周人先公公刘在豳时期,依然去渭河以南活动,“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复修后稷之业,务耕种,行地宜,自漆、沮度渭取材用。”[1]
西周时,“岐沣之域”是西周最核心的地带,而这一地带的中心就是今周至县渭河南原一带,这不仅仅是地理的中心。周人从岐周到丰镐,经常从哪里渡过渭河呢?笔者认为就是周至、眉县接壤一带的渭河南北岸之地。先周时期,周人就从此南渡渭河,周至县也成为周人的活动核心区。渭河越是靠近下游,水量越大。在先周、西周时期,渡河技术不会很高,从周至、眉县一带水量较小的地方南渡渭河比较有利,这与西周以后从咸阳南渡渭河是不同的。
岐周到丰镐的大道要经过今周至,竹峪一带成为重要的城邑乃至一度建立了“盩先王宗庙”,这与当地地形密切相关。关中渭河以南,从西安到周至的渭河平原在汉代称为“陆海”,地下水位高,水源丰富,从秦岭北麓注入渭河的河流较多,低平的地方不易居住,而竹峪一带的台原,比其东面、北面的渭河平原要高,排水便利。
西峪遗址是周至县竹峪一带最重要的遗址,俗称“殿址疙瘩”,2013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十年来,当地出土了西周半圆素面瓦当、秦代葵纹瓦当、汉代云纹瓦当、文字瓦当,汉代回纹砖、乳钉砖、陶水管等,其附近还出土了大量青铜器,有西周早期的此母觯、父丁爵、饕餮纹爵,西周中后期的太师簋,西周中晚的窃曲纹鼎,西周晚期的作姜氏尊簋等。2006年以来,“盩先王宗庙”与西峪遗址的关系,便受到一些学者热切关注。
[1][西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3-114页。
五、“盩”地溯源
公叔祖类的庙为何讳为诸盩呢,“盩,引击也。从辛攴,见血也。”有勇猛之意,可知公叔祖类是周先祖中的一个英雄人物。施谢捷经过考证认为,商代甲骨文中即有“盩”字的原形,两种含义:“与习见的‘征’‘伐’相似;也可以用作人名国族名或地名。”“这一盩族人与周关系较密切,虽臣服于商,在征伐周族时,商王有意让他回避,而令‘龚’代替他。”[1]盩的最初含义可能是族名,与周关系密切,其地域包括今天周至县在内的渭河以南地区。
盩人可能与周人同祖,盩人与周人的主体隔着渭河,一度并行发展,最终盩人与周人融为一体,公叔祖类庙被讳为诸盩,表示周人对盩的强烈认同,“盩”也与“周”融为一体,盩地之名却保留了下来。
西周金文中多次出现“盩师”一词,其中《旅鼎》记述了西周康王时期召公征伐东夷,旅从征有功,召公在盩这个地方赏赐旅十朋。召公应该是在镐京向周王汇报之后,经过渭河以南向西行进,在盩这个地方对这次战争中立功的旅进行了封赏,最后再北渡渭河,故盩地应在周至县。[2]
总之,“二曲说”并非全无价值,“二曲说”的“山曲曰盩”观测立足点可能重点就在周至县竹峪台原一带;而“水曲曰厔”观测立足点也可能重点是指黑河以东众多弯弯曲曲的溪流上。秦人有以原坡为山的传统,秦汉时期的盩厔山就是指周至县竹峪台原一带的原地。盩厔为盩庙之意,诸盩是先周公叔祖类庙的讳称,周至县竹峪台原一带曾有过“盩先王宗庙”。盩人可能是一个族群,生活在包括今天周至县这一带在内的渭河以南地区,与周人同祖,一度与周人隔渭河而并行发展,最终完全融为一体。这就是我们对盩厔二字的解读。
[1]施谢捷:《释“盩”》,《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4期,第116页。
[2]唐兰:《论周昭王时代的青铜器铭刻》,《古文字研究》第二辑,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1-22页。返回搜狐,查看更多